姐从老家给我们寄来了两袋冻米。回家瘫在沙发上,抓一把送到嘴里,时空就会嗖的一下穿梭回去。
每回老妈老姐说要带东西过来,大包小包一大堆,我都说不用,现在科技这么发达,山珍海味蔬菜瓜果哪一个在首都还买不到呢?老妈就说,你看蛋是自己家的鸡下的,菜是自己家种的,小鱼都是亲戚朋友烘干的,辣鸡翅膀到乡下收的,鱼丸子是伯伯舅舅家自己打的……这里面吃的是一种情感,是一种关心。你要说真有多喜欢吃倒也不是,就是偶尔体会一下用钱换不回来的念想,文化人管这叫乡愁。
冻米是其中一种比较特殊的存在,百吃不腻五味杂粮,说不出来的感觉。冻米是我们老家的方言,用现在的话说其实就是爆米花,不同的是,冻米真的就是大米打出来的,不是玉米粒。至于为什么叫“冻米”,我也没从谁那听到个所以然,有可能叫“洞米”,也可能基于拟声所以叫“咚米”。这种简单的美食是我们小时候最期待的零食,尽管没有奶油,没有暴甜,但是那一丝丝的甜味也能引爆我们的味蕾。
我觉得发明了冻米机器的人是个人才,我曾经想着这一定是华夏文明历史悠久的见证,从古代开始一代一代把手艺流传下来,可能是第五大发明。后来我看到了机器上的那个压力计,指针随着温度的变化动来动去,让我心里的幻想一下破灭了,带有“现代化仪表”的物品,就跟一个印着“北京欢迎您”的青花瓷一样,都是一件煞风景的事。
我印象里,排队打冻米的场景是很热闹的。一群人抱着一个脸盆或者桶,里面装着自己家吃的大米(可能是粮票换的也可能是自己家种的),小朋友们手里拽着几毛钱,满脸兴奋,充满期待的眼神,闻着一路的飘香先解着馋。那些大妈老奶奶们一起叽叽喳喳,说这家闺女找了个当官的,那家小伙子跟人打架了,很少看到有爸爸们在那排,估计是一家之主的地位不屑于此。排的队伍一般都是老长,为了不影响公共交通,通常打冻米的师傅都会选在一个肉食加工铺门口的那个小坪地上,那时也没有城管赶人,一片祥和。那个肉食加工铺就跟街头霸王游戏里对阵春丽的背景一模一样,对面还有牌馆,以及阉鸡的老师傅坐在门口,戴着老花眼镜,一根铜勺从割开的公鸡后背上探进去,拿出了什么动物器官,那些鸡也不挣扎也不叫唤,就那么趴着,眼睛睁开看着人来人往。
从小坪地顺着街过去不到200米,就是两颗成了精的樟树,豪迈地喊着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黄巢打到了这里,把马系在了这两棵樟树上。然后它们活了千年,见证了太多历史,看到了起伏兴衰。它们变大了很多,需要十几个人合围才能抱住,也变老了很多,除了树根和树皮,里面什么都没有,从上面往里看,只看到黑乎乎一片空洞,奇怪的是每年春天依然发绿油油的新芽。
打冻米的师傅并不用叫卖,也不用宣传。一旦他把架子搭起来,把火升起来,大家就会自然的聚拢过来,然后一群人尖叫着辐射开来,就跟小蚂蚁一样把消息带给了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,催着自己的父母拿米拿钱。即便没人通知你,你也不可能不知道,一来这时的香味顺着街道飘散开了,二来最关键的是师傅那一脚,“砰”的一声炸开,比我们买的鞭炮声还大,能够把你从床板上震到地下。每次师傅要踩那一脚,我们都把耳朵捂住,又害怕又想看,眼睛偷偷地瞄着那个如葫芦一般黑不溜秋的铁罐。每砰的一声响,我们就开心地很,因为这意味着队伍又往前挪了一挪,大家就把家伙往前踢一踢。偶尔我们能看到一声响后会有人骂骂咧咧,大概率是骑自行车的人被突然一吓给整摔跤了。
不同的师傅感觉并不一样,有些特别严肃,有些人总是在抱怨,有可能是家里生的女儿太多,为了生活奔波的他似乎感受不到快乐,只是想赶紧赚钱养活家里,再多生一个可能就是男娃了。我觉得大部分师傅还是比较快乐的,他们坐在一个交叉形状的特别特别矮的折叠小凳子上,左手抽拉着鼓风机,呼呼作响,吹着炭火跟着节奏忽亮忽暗,右手转着洞米的铁罐,眼睛盯着跟着旋转着的压力仪表指针。那铁罐转啊转啊,没转一下就感觉离幸福生活的距离又近了一步,温度每高一点压力每增加一点,也感觉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期待,手不自主的加大了力道。没到火候他们就比较放松跟着我们闲聊生活的琐事,逗着大家伙玩,一看火候到了,把罐子对准着一个长长的网兜,网兜接着罐子的一头是用铁环和竹篓定型的大圆口,另一头是用绳子扎紧的软兜。师傅对着网兜口放进去,用一只脚踩着罐子,手上用一根铁棍压着,对着我们喊“走开点走开点……”,又是“砰”的一声,伴随着扑鼻而来热腾腾的香气,以及一片烟雾缭绕……师傅到网兜的另一头把绳子解开,把冻米倒进带过来的铁桶里,再又把绳子系上,开始服务下一个客人。
师傅接过了我们的米,倒进了铁罐子里,再倒入我根本看不清的约等于没有的糖精,把盖子盖上,在盖子的结合处抹上一些灰(哪怕上完了大学,至今我不知道用途和原理),把铁罐两端的铁棍驾到了两边半圆形的凹槽中,就跟烤羊肉串一般转了起来。我跟姐神气地抬起头,向世人宣告里面正在含苞待放的冻米是我们的,我能看到那些人眼里的羡慕嫉妒……不过几分钟,我们的神气时间就结束了。我总觉得别人的时间特别长,到我们这就是一会的功夫。还没来得及恼怒,看着一桶的冻米,我们伸手抓了一把,控制不住的相视一笑。
肉铺小坪地早已不在了,牌馆也不在了,阉割鸡的戴老花镜的大爷更不在了。街道变得整洁安静,围着两棵老樟树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公园。如果不是看到空洞洞的樟树,我完全无法认出那条街道,因为那只剩下了一条街道,没有了喧嚣,没有了家长里短,没有了我跟姐去帮老妈收摊时偷吃的场景。
我跟姐说,冻米还是很好吃,只是没有以前甜了,姐说她们说放糖的给小孩吃了不好,我就要他别放了。
本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(赵武的自留地):冻米
- 左青龙
- 微信扫一扫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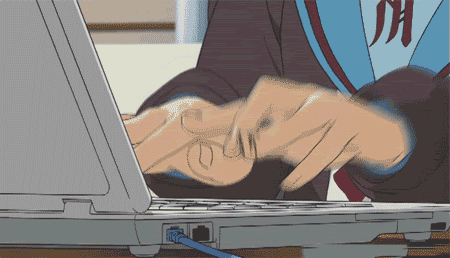
- 右白虎
- 微信扫一扫
-



评论